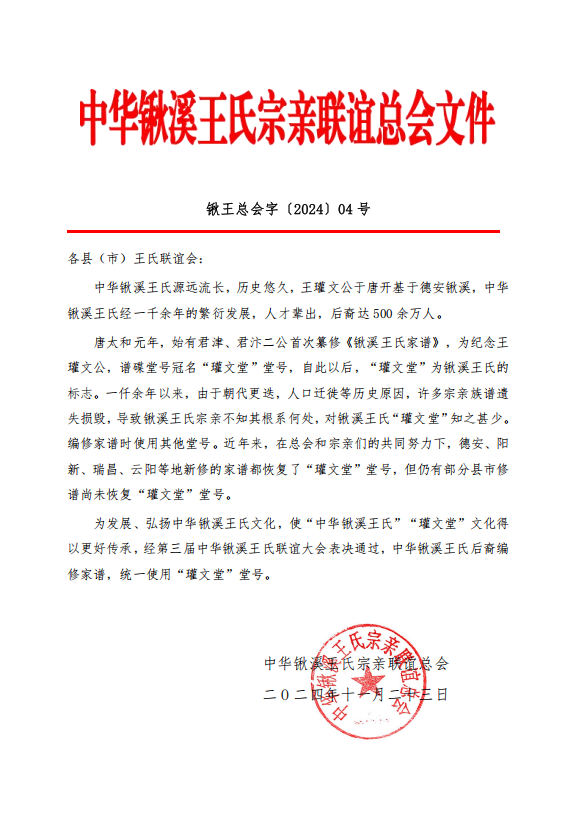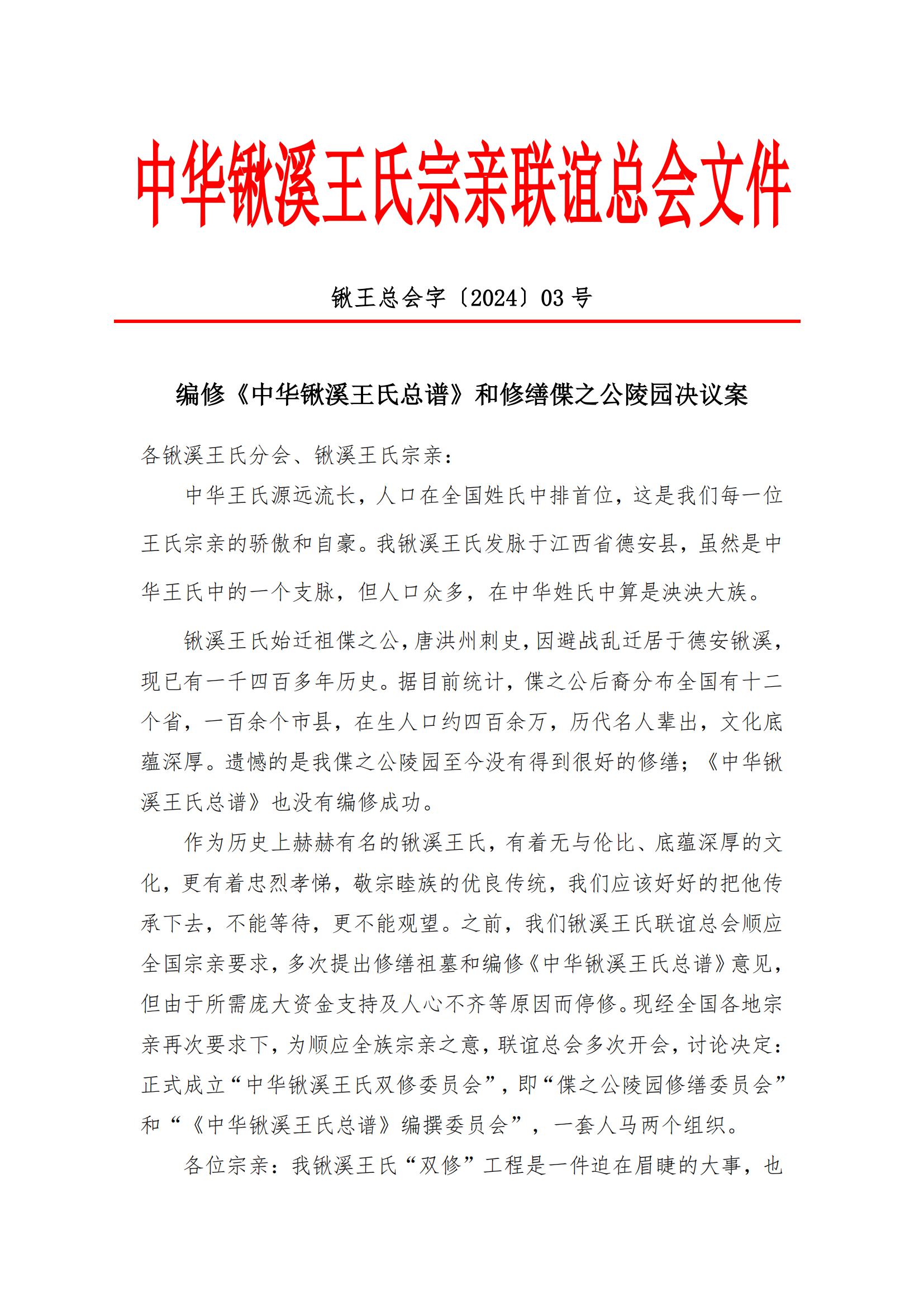阅读排行
- 第三届中华锹溪王氏联谊大会表彰名单12-02
- 王韶墓群重修集资:铜鼓县三都交古村 400元 06-29
- 王韶墓群重修集资:湖北通山县茅田王氏宗亲会首批累计80000元06-29
- 王韶墓群重修集资:永修县艾城镇阳山村上组 840元 06-29
- 王韶墓群重修集资:瑞昌市南义镇王福庄 1600元 06-29
- 王韶墓群重修集资:九江市修水县渣津镇朴田村石人片王坑庄 2400元 06-25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有益 1000元 湖北通山车田庄06-22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需民 1000元 江西德安06-22
- 王韶墓群重修集资:九江市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龙岗组 1280元 06-22
- 王韶墓群重修集资:南昌市新建区黄堂王氏 20000元 06-22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旭庆 2000元 江苏金坛06-03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玉忠 1000元 江苏金坛06-03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玉明 1000元 江苏金坛06-03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有然 2000元 湖北通山县06-03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定笔 5000元 湖北通山县06-03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定钊 2000元 湖北通山县06-03
- 王韶墓群重修捐资:王定乾 5000元 湖北通山县06-03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有泉(友全) 2000元 河南新蔡县孙召镇张楼村大马营05-2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义 200元 德安县塝上庄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财 200元 德安县塝上庄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银 200元 德安县塝上庄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雷 200元 德安县塝上庄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生 500元 德安县塝上庄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雄 1000元 德安县塝上庄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河 500元 德安县邹桥坂庄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江 2000元 德安县邹桥坂庄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红安县王氏联谊分会(印谱余) 2240元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巾口乡巷口庄 600元 武宁县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巾口乡蒜洲庄 800元 武宁县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巾口乡山下庄 470元 武宁县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巾口乡艾冲庄 680元 武宁县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巾口乡栎庄 660元 武宁县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船滩梓坪庄 480元 武宁县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船滩新店庄集资 760元 武宁县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大垅庄集体集资350元 瑞昌市黄金乡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界首庄(二次)3180元 瑞昌市黄金乡05-1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勇两次计 1000元 黄石市阳新县王志村九组(邮政局)05-14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有义(宥贻) 2100元 黄石市阳新县半山王庄05-09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松贤1000元 瑞昌市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益波1000元 瑞昌市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效贤1000元 瑞昌市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忠炎500元 江西省九江县王据湾庄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志500元 湖北省英山县六君王氏(在校小学生)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正军2000元 湖北省英山县林业局副局长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智2000元 湖北省英山县智中和董事长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长虹庄集体捐款1800元 湖北鄂州市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长虹庄交集资款2000元 湖北鄂州市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集资款:王荣哲代交集资款5000元 安徽省金寨县古碑镇七邻村王氏01-1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 王金水 200元 杨家湾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林 200元 杨家湾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林 200元 杨家湾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坤500元 杨家湾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定国 1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淼生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勇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 王定杉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珍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铭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南生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喜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欢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定松 2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友 3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友 3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友 3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友 3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友 3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能才 4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有勤 5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定桂 5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钊 5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华 500元 潘师畈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金 100元王家棚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海 200元 王家棚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忠煌 500元 中源坳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忠辉 600元 中源坳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修德 5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忠心 5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葛金宝 5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 王能清 5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周文亮 5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平 5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罗成 5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成 10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忠兴 20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忠贵 20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保 3000元 锹溪庄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淼 500元 郑塘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智 500无 郑塘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三毛 500元 郑塘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金德 600元 郑塘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有舟 1000元 郑塘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勇 1000元 郑塘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烈寿 1000元 深坑垅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先林 1000元 深坑垅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先干 1000元 深坑垅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定勇 200元 九井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义先 300元 九井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贤满 500元 九井08-02
- 锹溪王氏宗祠捐款:王红金 500元 九井08-02
王寀与《汝帖》
李志军
神童
可以说,宋代以后,所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都受到了王寀的影响。
岳珂的《桯史》里面有一篇文章“南陔脱帽”。“南陔脱帽”,与“文彦博灌穴浮球”、“司马光破瓮救儿”,都是千古流传的神童故事。
南陔就是王寀,北宋著名的才子。
王寀(1078—1118),又名王癭,字辅道,一字道辅,号南陔。
南陔,出自《诗经·小雅》。六笙诗之一,有目无诗。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为前三篇,是燕飨之乐。《诗·小雅·南陔序》:“《南陔》,孝子相戒以养也;《白华》,孝子之絜白也;《华黍》,时和岁丰,宜黍稷也。有其义而亡其辞。”
《桯史》载:
“神宗朝,王襄敏(韶)在京师,会元夕张灯,金吾弛夜,家人皆步出将帷观焉。幼子(寀)第十三,方能言,珠帽襐服,冯肩以从。至宣德门,上方御楼,芗云彩鳌,箫吹雷动,士女仰视,喧拥阗咽,转盻已失所在,驺驭皆恇扰不知所为。家人不复至帷次,狼狈归,未敢白请捕。襄敏讶其反之亟,问知其为南陔也,曰:‘他子当遂访,若吾十三,必能自归。’怡然不复求。咸叵测。居旬日,内出犊车至第,有中大人下宣旨,抱南陔以出诸车,家人惊喜,迎拜天语。既定,问南陔以所之。乃知是夕也,奸人利其服装,自襄敏第中已窃迹其后。既负而趋,南陔觉负已者之异也,亟纳珠帽于怀。适内家车数乘将入东华,南陔过之,攀幰呼焉。中大人悦其韶秀,抱置之膝。翌早,拥至上阁,以为宜男之祥。上问以谁氏,竦然对曰:‘儿乃韶之幼子也。’具道所以,上顾以占对不凡,且叹其早惠,曰:‘是有子矣。’令暂留,钦圣鞠视。密诏开封捕贼以闻,既获,尽戮之。乃命载以归,且以具狱示襄敏,赐压惊金犀钱果,直钜万。其机警见于幼年者,已如此。南陔,寀自号,政和间有文声,敢为不诎,亢其幼者也。余在南徐,与其孙(遇)游,传其事。”
王寀五岁时,元宵夜,戴着珠帽,由家人驮着看花灯,被贼人盯上了。皇上登楼,万民涌动。贼人乘机把王寀从仆人的肩膀上架了过来。一会儿,王寀觉得不对,一看是个陌生人,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,也不作声,先把珠帽藏在怀里,又在贼人的衣领上悄悄做了记号。碰巧神宗皇帝的车辇通过,他便攀车呼救。贼人吓得扔下小孩,赶快逃走了。第二天,神宗让太监把他抱来询问。王寀说:“儿乃王韶之子。”皇帝看他聪明大方,很是喜爱,又正想要个儿子,把王寀当成了送子观音的童子。留在宫中玩了半个月,才送回家去,赏了好多钱压惊。这便是“压岁钱”的由来。现在我们的每一个人,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,都会因为王寀的缘故,而定期享受到生活的幸福和快乐。
岳飞的孙子岳珂与王寀的孙子王遇是好朋友,就把此事记载了下来。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有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的传奇,讲的就是王寀的故事。
王韶
北宋嘉佑二年(1057),在欧阳修的主持下,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一次科举考试,被称为“龙虎榜”。其中,有十个非凡的同榜进士。苏轼、苏辙兄弟,加上曾巩,文学“唐宋八大家”,占了三个。程颢、程颐(次年赐进士)兄弟,加上他们的表叔张载,哲学“北宋五子”,占了三个。还有三个宰相,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。另外一个就是王寀的父亲王韶。
王韶(1030-1081),字子纯,江西德安人。王韶是一位奇人,中进士后不做官,每年都要跑到西北边境上流浪,他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家照料七个儿子,以至于病死,其中一子送入,家后的山至今名叫“望夫山”。
当时北宋的主要敌人是西夏。两国战争不断,宋朝胜少负多,包括范仲淹也只有采取守势。
治平四年(1067年)正月,宋英宗驾崩,太子赵顼继位,次年改元熙宁。
宋神宗幼时,便知祖宗志吞幽,蓟、灵武,而数败兵,立志雪数世之耻,慨然兴大有为之志,思欲问西北二境罪。
此时,王韶在西北已经整整游历考察了十年。熙宁元年(1068),王韶上《平戎策》,提出收复河、湟,招抚戎羌,孤立西夏的方略,为宋神宗所纳。
《宋史》载:
“熙宁元年,诣阙上《平戎策》三篇,其略以为:‘西夏可取。欲取西夏,当复河、湟,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。夏人比年攻青唐,不能克,万一克之,必并兵南向,大掠秦、渭之间,牧马于兰、会,断古渭境,尽服南山生羌,西筑武胜,遣兵时掠洮、河,则陇、蜀诸郡当尽惊扰,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?今唃氏子孙,唯董毡粗能自立,瞎征、欺巴温之徒,又法所及,各不过一二百里,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!武威之南,至于洮、河、兰、鄯,皆故汉郡县,所谓湟中、浩亹、大小榆、枹罕,土地肥美,宜五种者在焉。幸今诸羌瓜分,莫相统一,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。诸种既服,唃氏敢不归?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。且唃氏子孙,瞎征差盛,为诸羌所畏,若招谕之,使居武胜或渭源城,使纠合宗党,制其部族,习用汉法,异时族类虽盛,不过一延州李士彬、环州慕恩耳。为汉有肘腋之助,且使夏人无所连结,策之上也。’神宗异其言,召问方略,以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。”
在王安石的支持下,王韶镇守西北边境,大败吐蕃,平定羌乱,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。收复熙、河、洮、岷、叠、宕六州,回归故土二十万平方公里,取得了北宋有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。八年,任枢密副使,被称为奇计、奇捷、奇赏“三奇副使”。
《宋史》载:
“五年七月,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,破蒙罗角、抹耳水巴等族。初,羌保险,诸将谋置阵平地,韶曰:‘贼不舍险来斗,则我师必徒归。今已入险地,当使险为吾有。’乃径趣抹邦山,压敌军而阵,令曰:‘敢言退者斩!’贼乘高下斗,师小却。韶躬披甲胃,麾帐下兵逆击之,羌大溃,焚其庐帐而还,洮西大震。会瞎征度洮为之援,余党复集。韶命别将由竹牛岭路张军声,而潜师越武胜,遇瞎征首领瞎夔等,与战破之,遂城武胜,建为镇洮军。进右正言、集贤殿修撰。复击走瞎征,降其部落二万。更名镇洮为熙州,以熙、河、洮、岷、通远为一路,韶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。”
王韶胆略过人。“尝夜卧军帐中,前部遇敌,矢石交下,呼声震山谷,侍旁者往往股栗,而韶鼾息自若。”
《宋神宗褒奖王韶的八道敕》之四:
“朕既赏其身矣,今又录其诸子,及命尔秩,于京办寄,以效忠勤,以荣尔父。朕于士大夫可以无负矣。特赐韶长子廓进士出身,次子厚俱大理评事,完、固、端、孚、定、确、实、癭俱承务郎。熙宁七年七月□日奉特旨。”
宋神宗褒奖王韶,特赐韶长子王廓进士出身,次子王厚俱大理评事,其他儿子俱承务郎。承务郎为文散官第二十五阶,从八品下。王寀任“承务郎”时,年方七岁。
王安石变法失败后,旧党得势,王韶被贬知洪州,迁知鄂州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拜观文殿学士、知洪州,封太原郡开国侯。元丰四年(1081年),王韶去世,年五十二,追赠金紫光禄大夫,谥号“襄敏”。政和四年(1114年),追赠太尉、司空、燕国公。
王韶是一位诗人。《咏裕老庵前老松》诗云:
“绿皮皱剥玉嶙峋,高节分明似古人。解与乾坤生气概,几因风雨长精神。装添景物年年换,摆捭穷愁日日新。惟有碧霄云里月,共君孤影最相亲。”
晚年,王韶参禅悟道,是临济宗黄龙派得法弟子(为风穴延沼下第六代弟子),与黄庭坚是同门师兄弟。
《五灯会元》载:
“观文王韶居士观文王韶居士,字子淳,出刺洪州,乃延晦堂问道,默有所契。因述投机颂曰:‘昼曾忘食夜忘眠,捧得骊珠欲上天。却向自身都放下,四棱塌地恰团圆。’呈堂,堂深肯之。”
苏轼、苏辙兄弟虽然与王韶政见不同,对王韶十分敬重。
王韶病故后,苏辙代知筠州毛维瞻写有《代毛筠州祭王观文韶文二首》。其一云:
“公学敦诗书,性喜韬略。奋迹儒者,收功戎行。千里开疆,列鼎而食。丰功伟烈,震耀当年。绛纛朱幡,留连列郡。用舍之际,方共慨然。存没之来,孰云止此。子幼方仕,母老在堂。百口有藜藿之尤,十年为梦寐之顷。士夫殒涕,道路兴嗟。某比缀末姻,仍叨属部。笑言未接,涕泣长辞。攀望灵车,寄哀薄奠。伏惟尚飨。”
又云:
“嗟人之生,梦幻泡影。短长得失,何实非病。惟公少年,阔略细行。従军西方,睥睨邻境。手探虎穴,足践荒梗。遂开洮岷,归执兵柄。功名赫奕,富贵俄顷。未安西枢,斥就南屏。盘桓武昌,偃息洪井。国方用兵,边鄙未靖。谓当再驾,没齿驰骋。呜呼不淑,一寐不醒。老幼盈前,饘粥谁省。盛衰奄忽,惊怛群听。惟公晚年,自谓见性。死生变化,其已安命。世之不知,奔走吊庆。寄奠一觞,孰为悲哽。尚飨。”
王寀
王寀于徽宗崇宁二年(1103)登进士第,由曾布、蔡京荐入馆为秘书省著作左郎,曾知汝州、陕州、襄州,任翰林学士,兵部侍郎。
王寀才思敏捷,为北宋诗坛名流。宋代洪迈的《夷坚志》卷第八也记载了一个故事:
曹道冲售诗京都,随所命题即就。群不逞欲苦之,乃求浪花诗绝句,仍以红字为韵。
浪花是蓝色的,却要以“红”为韵,难度很大。曹道冲作不出来,说:“只有翰林学士王寀能作出来。”群不逞说:“我久闻大名。但他是馆阁大臣,我辈小人,他会接见我们吗?”曹道冲说:“带上好纸好笔试一试。”王寀欣然捉笔,一挥而成,读者叹服。《浪花》诗云:
“一江秋水浸寒空,渔笛无端弄晚风。万里波心谁折得,夕阳影里碎残红。”
王寀写了很多词。《浣溪沙》:
“雪里东风未过江。陇头先折一枝芳。如今疏影照溪塘。北客乍惊无绿叶,东君应笑不红妆。玉真爱着淡衣裳。”
政和六年(1116)秋,王寀游山西紫团山,作有《题紫团山三十六景》诗。自食(上午7-9)至晡(下午3-5),三十六景赋之遍,改动一二字耳。今《全宋诗》之王癭诗即据此辑得。
王寀是著名的书法家,所写诗稿被刻成石碑。《山西通志》称其字“神奇”。原刻十二石,止存四石。顺治十八年,知县朱辅移置学宫。
王寀遭人陷害,身陷囹圄时,狱卒们纷纷带着纸笔求墨宝。狱卒说:“昔苏学士坐系乌台,时狱吏实某等之父祖。苏学士既出后,某恨不从其乞翰墨也。”
可见,当时王寀的书名与苏轼不相上下。只不过王寀之书,上溯二王,有魏晋之清雅,而法度严谨,规范于唐人,不入宋代“尚意”书风时流,为后人忽视。
王寀的书名埋没于后,与他是朝廷要犯有关。当年苏东坡列入“元祐党人”,被视为罪犯时,苏东坡的墨迹也一应销毁,私藏者视同犯罪。不过苏东坡不久即昭雪,而王寀的孙子曾为爷爷上下申冤,朝廷予以平反却又半道追回。
王寀被斩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。政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,宋徽宗皇帝亲自下诏将其斩首。诏曰:
“王寀儒馆通籍,勋阀之后,而议论交通踪迹,往复诗歌酬唱,辞所连逮者三十人,悖逆不道,谤讪妖讹,载籍所未尝有,人臣所不忍闻。”
《宋史·王寀传》中说:
“(王寀)忽若有所睹,遂感心疾,唯好延道流,谈丹砂神仙事。得郑州书生,托左道,自言天神可祈而下,下则声容与人接。因习行其术,才能什七八,须两人共为乃验。外间欢传,浸淫彻禁庭。徽宗方崇道教,侍晨林灵素自度技不如,愿与之游,拒弗许。户部尚书刘昺,癭外兄也,久以争进绝还往,神降癭家,使因昺以达,寀言其故,神曰:‘第往与之言,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后堂谈某事,有之否?’昺惊骇汗浃,不能对,盖所言皆阴中伤人者。乃言之帝,即召寀,风仪既高,又善谈论,应对合上指。帝大喜,约某日即内殿致天神。灵素求与共事,又弗许。或谓灵素,但勿令郑书生偕,寀当立败。即白帝曰:‘寀父兄昔在西边,密与夏人谋反国。迟至尊候神,且图不轨。’帝疑焉。及是日,癭与书生至东华门,灵素戒阍卒独听癭入。帝斋洁敬待,越三夕无所闻,乃下癭大理,狱成,弃市。”
王寀因心疾迷惑,好神仙道术。但徽宗皇帝是一个著名的道教皇帝,延揽道士,访求仙经,兴宫观,筑艮岳,以“教主道君皇帝”自尊,决不会因为王寀“议论交通踪迹”——即与神仙相沟通——而将他置于死地。里面定有隐情。
林灵素(1075~1119),原名灵噩,字通叟,温州(今属浙江)人,北宋末著名道士,少时曾为苏东坡书僮。东坡问其志,笑而答曰:“生封侯,死立庙,未为贵也。封侯虚名,庙食不离下鬼。愿作神仙,予之志也。”据《家世旧闻》记载,“少尝事僧为童子,嗜酒不检,僧笞辱之,发愤弃去为道士”。林灵素既得召见,徽宗问:“有何术?”答曰:“臣上知天宫,中识人间,下知地府。”又进言:“天有九霄,而神霄为最高,其治曰府。神霄玉清王者,上帝之长子,主南方,号长生大帝君,陛下是也,既下降于世,其弟号青华帝君者,主东方,摄领之。己乃府仙卿褚慧,亦下降佐帝君之治。”并称权臣巨阉如蔡京、王黼、童贯等皆为仙官。时贵妃刘氏有宠,则奉为九华玉真安妃。
宋徽宗赐号“通真达灵先生”,加号“元妙先生”、“金门羽客”。林灵素恃宠横行霸道,与诸王争道,甚至冲撞太子,因嫉妒毒死道士王允诚。
对林灵素的行径,王寀不以为然。《挥塵后录》称:“辅道(王寀)尝对别客谓灵素太诞妄。”
林灵素是心术不正之小人,屡屡巴结王寀不上,当然对其恨之入骨,故进谗言说“王寀谋反”。林灵素与开封府尹盛章勾结。盛章陷害王寀的外兄户部尚书刘昺。《挥麈后录》卷三载:
“翌日,章以急速请对,因言:‘寀与炳(即刘昺)腹心诽谤,事验明白,今对众越次,上以欺罔陛下,下以营惑群臣,祸将有不胜言者,幸陛下裁之。’上始怒。是日有旨,人侍省不得收接刘炳文字。炳未知之,以为事平矣,故不复闲防。章既归,遣开封府司录孟彦弼携捕吏窦鉴等数人即讯炳于家。炳囚服出见,分宾主而坐,词气慷慨,无服辞。彦弼既见其不屈,欲归,而窦鉴者语彦弼曰:尚书几间得□一纸字足以成案矣。遂乱抽架上书,适有炳著撰稿草,翻之至底,见炳和辅道诗,尚未成,首云:‘白水之年大道盛,扫除荆棘奉高真。’诗意谓辅道尝有嫉恶之意,时尚道,目上为‘高真’尔。鉴得之以为奇贷,归以授章,章命其子并释以进,云:‘白水,谓来年庚子(1120)癭举事之时,炳指为高真,不知以何人为荆棘,将置陛下于何地?岂非所谓大逆不道乎?‘但以此坐辅道与客皆极刑。炳以官高,得弗诛,削籍窜海外。”
可以肯定的是,王寀的罪名,纯属“莫须有”。其依据,仅是对“多年以前王寀的父兄曾与西夏谋反”的猜疑。
赵匡胤、赵光义兄弟均以不正当手段夺去别人的天下,所以对武将极为猜忌。赵匡胤说:“一百个文官贪污,抵不上一个武将造反。”赵广义说:“外忧不过边事,皆可预防;惟奸邪无状,若为内患,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,常须谨此。” 北宋另一位名将狄青,就是受到皇帝猜忌,抑郁而终的。
寀父王韶以军功起家,曾位居枢密副使。哥哥王厚,为节度使,边关元帅。王寀任兵部侍郎,兵权在手,就是无人陷害,恐怕也难逃厄运。史称王寀“少豪迈,有父风”,“轻财仗义,好结交天下士”,“宾客多归之”。他为人耿直,又口无遮拦,正好授人以柄。王寀的哥哥更是离奇,忽一日,因吃萝卜呕吐而死。
王寀获罪后,其所交往之文人雅士多被牵连,包括著名词人周邦彦,幸得蔡京相救,免得一难。
有个叫颜博文的画家,将所藏王寀手迹悉数焚毁,方逃过一劫。
岳飞平了反,王寀却没有。王韶和王安石互为倚重,都是变法的新党,王韶取得战争的胜利,皇帝把自己的玉带赏给王安石。在《宋史》上王安石是被列入“奸党传”的,连蔡京的儿子也说父亲和王安石不是一党。王寀的哥哥王厚也是战功累累的名将,监军却是童贯;王寀又和蔡京是好朋友。非常不幸,他们一家都是和历史上“公认”的奸臣搅在一起,难怪其功勋和声名就被埋没了。
千古一帖
自六朝迄今,皇家、书家、文人、收藏家、乃至商贾所刻的丛帖和单帖有千种以上。仅宋代,历史记载的就有五六十种。在这么多法帖中间,《汝帖》以其鲜明的主题,独树一帜,可谓是“千古一帖”!
在宋代,最为著名的莫过于《淳化阁帖》、《泉州帖》、《绛州帖》、《大观帖》、《汝帖》等五帖。
《淳化阁帖》简称《阁帖》。汇刻丛帖。十卷。公元992年宋太宗出秘阁(帝王收藏图书处)所藏历代法书,敕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摹刻而成。此后历代多有翻刻。虽采择未精,但古人法书颇赖之以传。自此刻帖盛行,后世因称此帖为“法帖之祖”。
《绛帖》为北宋潘师旦摹刻,因刻于绛州,故名,刻于1049--1063年(宋皇祐、嘉祐年间),以《淳化阁帖》为底本而有所增删。
《潭帖》,亦称“长沙帖”。北宋 庆历 间 刘沆 帅 潭州(今 湖南省 长沙市)时,命僧希白摹刻。计十卷。以《淳化阁帖》为底本,增入 晋 王羲之《霜寒帖》、《十七帖》以及 王濛、颜真卿等帖。原石毁于南宋建炎年间。
《泉帖》,明曹昭舒明 等《新增格古要论》:“﹝泉帖﹞以《淳化法帖》翻刻於 泉州 郡庠。”
北宋大观三年(1109)由汝州知州王寀刻《汝帖》。此帖计有金石文八种,秦、汉、三国字体五种,六朝帝王书三十引,魏 晋 九人书以及王羲之十帖、南唐十臣、唐三朝帝后四书和 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贺知章、李后主、吴越王俶等七十余家书法,一百零九帖,刻十二石。先置官衙,后置于汝州望嵩楼中。明 末兵乱,楼焚碑残。清顺治 七年(1650年)巡道范承祖重新修葺,并加诗跋二刻,共十四刻,置于州署西园古轩壁中。道光 十八年(1838年)州守白明义 见所存文漫漶不复识,自洛阳得《汝帖》原拓一部,重摹诸石,仍藏左轩壁中。现存汝州市博物馆中。
其它四帖,都是《淳化阁帖》的翻刻和复制。其目的,主要是学习书法。《汝帖》不同。
王寀《汝帖跋》:
“来汝逾年,吏民习其疏拙,不堪委以事。闭阁萧然,奉亲之外,独念弃日偶得三代而下讫于五季字书百家,冠以仓颉,奇古、篆籀、隶草、真行之法略真,用十二石刻置坐啸堂壁。其论世正名于治乱之际,君子小人之分,每致意焉,识者谓之‘笔史’,盖使小学家流固以博古知义,不特区区近笔砚而已。大观三年八月上丁敷阳王寀记。”
我们对这一段短短的跋文进行逐句疏解,王寀及其《汝帖》的情操立现。
“来汝逾年,吏民习其疏拙,不堪委以事。”——无为而治。
无为而治,是为政的最高境界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:“无为而治者,其舜也与?夫何为哉?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
“闭阁萧然,奉亲之外。”——孝道。
“独念弃日偶得三代而下讫于五季字书百家,冠以仓颉,奇古、篆籀、隶草、真行之法略真,用十二石刻置坐啸堂壁。”——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
“其论世正名于治乱之际,君子小人之分,每致意焉,识者谓之‘笔史’。” ——笔史。
“正名”出自《论语·子路篇》中。子路曰:“卫君待子而为政,子将奚先?”子曰:“必也正名乎!”东周以来,纲常大坏,整个社会处于相互杀戮的混乱状态。司马迁说:“春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”孔子周游列国,宣扬仁政,劳而无功,退而著《春秋》。孔子说:“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絮絮叨叨讲仁义道德,惹人讨厌,不如把自己的道德标准放在史书里面,让后人以史为鉴。孟子说: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乱臣贼子惧。”
汉代以后,《春秋》就是国家宪法。处理事件就要看《春秋》里有没有类似的故事,研究一下孔子的态度,这就是所谓“《春秋》决狱”。《三国演义》里面,华容道关羽之所以放走曹操,就是因为曹操讲了一个《春秋》故事。
郑国和卫国打仗。卫国的庾公追杀郑国的孺子。孺子说:“今天我的病发作了,无法拿弓。”庾公便抽出箭来,在车轮上敲掉箭头,射了四箭之后返身回去了。在至高无上、亘古不变的《春秋》大义面前,军法乃至国法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关羽尽管冒着斩首的危险,却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。
孔子把自己的看法含蓄地寄托在历史故事里面,这就是“《春秋》笔法”,“微言大义”。
王寀是以孔子作《春秋》为楷模,借“笔史”而“论世正名于治乱之际,君子小人之分”。
懂一点历史的人心中都明白。唐末以后,五代十国,也是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毫无节操道德可言。包括赵家的天下的获得,赵匡胤的“黄袍加身”,赵光义的“烛光斧影”,都是谋纂而来。
宋代的读书人,都有和王寀一样的卓越胆识和道德理想。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,王寀刻《汝帖》,其目的,都是明天道,叙人伦,重建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。
欲“正名”,须从“文字”着手。再往下看。
“盖使小学家流固以博古知义,不特区区近笔砚而已。” ——小学。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文字”为“经艺之本,王政之始”。后魏江式《论书表》云:“夫文字者,六艺之宗,王教之始。前人所以垂后,今人所以识古。故曰‘本立而道生’。孔子曰:‘必也正名。’”
小学分为训诂,字书,韵书三类。主要为了理解经义。王羲之著有《小学章》。姜夔《绛帖平》中说:“小学既废,流为法书。法书又废,唯存法帖。法帖乃古人陈迹耳。”
王寀将《汝帖》的定位,首先是为明经达理之用,其次是书法,再次才是法帖。
“大观三年八月上丁。”——上丁。
这个落款也大有深意。上丁,指农历每月上旬的丁日。唐代以后,每年仲春(二月)、仲秋(八月)上丁日,为祭孔之日。
与《汝帖》的以“春秋大义”而陶铸“笔史”相比,宋代其它诸帖,立意浅陋,买椟还珠,不过是“区区笔砚”,“古人陈迹耳”。
宋曹士冕《法帖谱系》说:宋太宗以武定四方,而立文治,留意翰墨。书法对于宋太宗,倒是“以文化成天下”的一部分。可惜负责编纂《淳化阁帖》的王著没有学问。黄庭坚说:“王著临《兰亭序》、《乐毅论》,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,皆妙绝,同时极善用笔。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,不随世碌碌,则书不病韵,自胜李西台、林和靖羙。羙而病韵者王著,劲病韵者周越,皆渠侬胸次之罪,非学者之不尽功也。”
王著苦不读书,虽然用笔精妙,而无内涵,经他的手摹刻出来的法帖,“但得形范,而无神妙”。
刘公沆的《潭帖》,潘师旦的《绛帖》,都是《淳化阁帖》的复制和增删。
蔡京与王寀本是好友,《汝帖》与《大观帖》同刻于大观三年,而志趣迥异。《大观帖》是对《淳化阁帖》稍加修订的翻刻,并无主观的人文因素附加于内。
《大观帖》被誉为“古代刻贴第一精品”,不过是“金石之工”,摹写镌刻更加准确而已。
王寀则是文以载道为主旨的新的艺术创造。作为“笔史”,《汝帖》的编排上,与《淳化阁帖》不同,全帖按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。内容上,全面而均衡。商、周铭文、秦、汉刻石、魏、晋手札、北朝碑刻,几乎应有尽有。
在《汝帖》里面,《淳化阁帖》仅选入了三分之一。《淳化阁帖》十卷,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二人共占五卷。而《汝帖》十二卷,二王父子仅有一卷。而增加了诸如梁鹄、诸葛亮、“竹林七贤”、颜真卿等忠臣、高士、烈士书法。
马玉兰在《宋代法帖所反映的宋人书史观念》中说:“最值得称道的是《汝帖》首次将北朝人书模入丛帖。”北朝的书法,在当时是被排斥的。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说:“虽差近古,然终不脱毡裘气。”欧阳修《集古录》中说:“亦意其夷狄昧于学问而所传讹谬尔,然录之以资广览也。” 马玉兰说,今天人们常常认为清朝阮元在《南北书派论》中的阐述,是首次将北朝碑版与六朝简札作等量齐观,把北朝书法推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,实际上忽略了《汝帖》在这方面的贡献。可以说,碑派书学,应溯源到八百年前的《汝帖》!
《汝帖》为人所诟病处,乃其伪帖。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是黄伯思的《东观余论》。董其昌说:“无帖不伪。”不说《淳化阁帖》,就连《三希堂法帖》也难以幸免。其实,王寀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,称其所收集到的“略真”,只是他所关注的不是真伪问题。
在艺术成就上,《汝帖》自有独到之初。王文治《快雨堂题跋》称《汝帖》:“神采迸露,远出世俗所传《绛》、《潭》诸刻之上。”又说:“余尝谓古帖中,有以摹拓至精而传神者,亦有以摹拓粗漫而传神者,此帖全以粗漫传神。”
关于“粗漫传神”,施安昌先生说:“粗漫不是粗糙、草率,应是浑脱、浩荡的意思。”余彦焱先生《〈汝帖〉述略》中有大段议论。撷其要,即是“求生,求变,以学问、修养入书,而非以书法为定技”,“脱去右军父子习气”,“是一种有深厚内涵的境界”。
王寀学兼儒道释,擅长诗文,精通书画,学养深厚,倾注着崇高的文化道德理想,《汝帖》所刻的书迹纯中锋运行,线条雄健,内力充沛,神采飞扬,与小心谨慎的皮相摹勒气象迥异。
王铎曾于亲翁家席上闻歌酒斝近花籬之傍,“再观此帖,喜意发扬。真乃稀世之宝,超迈无伦。”
《汝帖》无论从内容上,精神上,还是艺术成就,都堪称“千古第一帖”!
王寀在汝州
王寀在汝州虽然仅有三年,政绩突出。据好友李廌的诗文记载,王寀开挖了“太史湖”,并组建“娘子军”进行操练,比赛射箭。
“汝州刺史宅引牛山水为池,于石穿牙城之东,窦而入于堑。然其防岸垫缺,土堙水秽,或漫浸民室。自丞相富公领州以来,欲治未遑。他日郡置铸钱官,派水共用,除归于池,水溢大,池窦不能容泄,则又有决溢之虑,公私病之。今太守德安王公慨然曰:‘郡以水名,而汝有海称。且古语谓汝有三十六浸,是乃泽国。乌有吾池蹴步之外,辄使公私病之?亦政所当及也。’属岁二月举春令,命有司慎沟洫陂障,而以待时雨。于是因水所入,至水所出,源流汇委,一时浚治。发故窦为门栅关键,以限内外。广故堑为湖,方行五舟。表景三十余刻乃遍,其深有倍寻者。堤高恒有五尺,长二千步,杂植佳木弥望,命之曰‘万家堤’。并门架桥,上可过车,下可通舫,命之曰‘万红桥’。引余波沟堤之南,注之州学。东与桥对,亦有沟,循昭惠庙,濡贯里巷,会南沟于通街之渠,流出东关,过东郭以入于黄陂。盖前日蓬雚薋菉之怒生,今槐柳交蔭,桃李成溪矣。前日蛙黽蚊蚋之閧集,今藻荇浮湛,鸥鹭翔戏矣。妙因佛刹,飞观复阁,映带其左。而古城乔木,樛枝苍干,蔽亏其右。汝阳楼据其北,少室、风穴诸山,又在其北。尊胜台控其南,崆峒、鲁阳诸山又在其南。陵波之亭,辛夷之洲,浮出于回塘菡萏之间。水光照衣屦,山色满欄楯。史君与客,步自西畴。临石濑,撷秋英。登舟于南陔之涘,循东西溪,所经皆竹里花坞。委蛇曲折,行锦罽罨画上度门至湖。忽空旷清明,如开奁出镜。云行日湛,鸢飞鱼跃,皆在镜中。遂为一郡胜处。客曰:‘此湖延袤,几与并汾柳堤等。而郡山浸碧,不减鄠杜渼陂。盍以嘉名之!’或曰:‘成州之房公湖,汉阳之郎公湖,所以为名,皆因太守。王史君于书无所不通,于文无所不能。妙龄擢上第,骤登瀛洲,领著作。熙宁以来史官日历,实与伦次。又尝以家学典治历,其成书曰《大观纪元》。论者谓史家三长,使君能兼之,俱绝人甚远,可谓善太史之职矣!宜以太史名之。俾而今而后,游览于斯者,想其风流于无穷,不宜可乎?’众曰:‘唯州园十二景,惟望高、香远为无恙,余但遗址而已。访之州人,虽少者犹及见之,而能指顾其处,然则其颓毁未远也。’”
李廌《汝州王学士射弓行》:
汝阳使君如孙武,文章绝人喜军旅。
要知谈笑能治兵,戏教红妆乐营女。
白毡新袍锦臂鞲,条脱挂弓腰白羽。
彩错旌旗照地明,傍花暎柳陈部伍。
须臾观者如堵墙,彷佛如临矍相圃。
一人中的万人呼,丝管呶嘈间钲鼓。
臂弓上为使君寿,遍及四筵乐具举。
使君一笑万众喜,堂上酒行堂下舞。
锦锻银荷翠玉钿,意气扬扬皆自许。
倘令被甲执蛇矛,恐可横行擒赞普。
大胜吴宫申令严,两队宫娃啼且怖。
阖闾台上呼罢休,将军虽贤亦觕卤。
岂知使君不忘战,聊以戎容娱尊俎。
夕阳卷旗去翩翩,使君要客登画船。
美人不暇别妆洗,战士结束围华筵。
皆疑征南汉将帅,楼船下濑方凯还。
军中不应有女子,偏禆校尉何其儇。
使君湖光照楼观,一碧不辨水与天。
渐看暝色著疏柳,已见白萍浮暮烟。
银汉斜横北斗淡,明月碧玉疏星联。
舟人罢唱时弄笛,艇子趁鱼行扣舷。
隔浦荧荧见渔火,意中竹篱青斾悬。
虽无荻花与枫叶,全似送客湓江壖。
亟令周娘作新曲,周娘琵琶京洛传。
不惜千呼与万唤,便时转轴仍拨弦。
冯夷阳侯或静听,穹龟大鱼或后先。
且言白傅时落寞,草草会遇仍嫣然。
使君闻名满台阁,虎符熊轼聊周旋。
风流乐事虽可记,皆过孙白二子前。
会看和戎竟先列,铁骑百万临三边。
报功女乐赐二八,粉白黛绿皆婵娟。
青云乞身归旧里,汾城故地依林泉。
琵琶亭中望汝海,无忘饮中今八仙。
 保存 |
保存 |
 打印 |
打印 |
 返回
返回